《乳品安全標(biāo)準(zhǔn)》(下稱"新《乳標(biāo)》")正在漸行漸近。伴隨新《乳標(biāo)》要求"巴氏消毒乳"標(biāo)識上標(biāo)"鮮",不僅與"由奶粉勾兌而成"的復(fù)原乳徹底區(qū)別開來;同時(shí),拉了大半年的"禁鮮令"警報(bào)也得以解除。
換句話說,一度握有乳業(yè)標(biāo)準(zhǔn)優(yōu)先話語權(quán)的"常溫奶陣營",反倒被以光明、三元為代表的"巴氏奶陣營"打了個(gè)翻身仗。
上海奶協(xié)副秘書長顧佳升分析,兩大陣營就是否標(biāo)"鮮"激辯多年,根源還在于制定乳品標(biāo)準(zhǔn)過于集中在檢驗(yàn)方法上,將"無法檢驗(yàn)"的"禁令性條款"砍掉,喪失了術(shù)語標(biāo)準(zhǔn)本身所具有的彌補(bǔ)盲區(qū)的功效。
廣州奶協(xié)會長王丁棉進(jìn)一步指稱,正因?yàn)槔@開了"禁令性"術(shù)語標(biāo)準(zhǔn),常溫奶陣營才能將常溫奶、復(fù)原乳、奶粉等非生鮮奶物質(zhì),打上"和巴氏消毒生鮮奶一樣都是好牛奶"的印記搶奪市場。
一波三折的保"鮮"戰(zhàn)
常溫奶包括"以生鮮牛奶為原料"的超高溫滅菌乳和"由奶粉勾兌而成"的復(fù)原乳,其特長在于保質(zhì)期長、價(jià)格較低,代表企業(yè)為伊利和蒙牛;而"以生鮮牛乳為原料,經(jīng)低溫殺菌處理"的巴氏奶,則以"鮮"取勝,典型企業(yè)為光明乳業(yè)和三元等。目前,常溫奶和巴氏奶的市場比例為7:3,而在數(shù)年之前,這一比例卻是3:7.
今年6月,蒙牛、伊利等乳企巨頭正開始主導(dǎo)制定乳品安全標(biāo)準(zhǔn),試圖以強(qiáng)制性標(biāo)準(zhǔn)的形式為復(fù)原乳正名,激起了巴氏奶陣營的強(qiáng)烈抗議。
一個(gè)月后,"巴氏奶陣營"成員聯(lián)合上書,直擊對手"要害"--如果復(fù)原乳標(biāo)志取消,或不在巴氏消毒奶上標(biāo)"鮮",消費(fèi)者將無法區(qū)別乳品原料是鮮奶還是由奶粉勾兌而成。
衛(wèi)生部和國家標(biāo)準(zhǔn)委員會均收到這份聯(lián)合建議書。不久后的8月5日,包括曾壽瀛、劉振邦以及顧佳升在內(nèi)的新《乳標(biāo)》制定小組成員被臨時(shí)召集到衛(wèi)生部開會,包括衛(wèi)生部、發(fā)改委、農(nóng)業(yè)部等在內(nèi)的十多個(gè)部委領(lǐng)導(dǎo)、專家共計(jì)70多人次參會。
更令曾壽瀛感到意外的是會議議題。曾壽瀛教授回憶:"巴氏奶陣營的聯(lián)合建議書和西部乳協(xié)的會議紀(jì)要被制作成幻燈片,在會上逐一討論。"
8月19日,衛(wèi)生部的態(tài)度發(fā)生了180度轉(zhuǎn)變,第一次站到了巴氏奶陣營這邊。巴氏奶陣營主張的"產(chǎn)品名稱分類可用到標(biāo)準(zhǔn)正式文本中"、"調(diào)制乳應(yīng)單獨(dú)制定相關(guān)辦法"以及"必須在標(biāo)識上區(qū)分巴氏消毒乳、滅菌乳以及復(fù)原乳"等建議被采納。
22日,曾壽瀛、王丁棉都表示,"禁鮮令"預(yù)警可以視作"基本解除".王丁棉解讀新《乳標(biāo)》指出,新《乳標(biāo)》雖然仍把復(fù)原乳納入到滅菌乳范疇,但它從標(biāo)識上將以鮮奶作原料的滅菌乳,與乳粉勾兌成復(fù)原乳為原料的滅菌乳(即常溫奶)加以區(qū)分,至少保全了消費(fèi)者的知情權(quán),巴氏奶陣營的核心競爭力也得以凸顯。
一旦區(qū)別標(biāo)注,很可能攤薄常溫奶的市場份額,給巴氏奶陣營提供發(fā)展良機(jī)。
缺少禁令性條款
從2008年12月起,衛(wèi)生部牽頭,會同十部門開始對乳品安全標(biāo)準(zhǔn)展開重新制定修訂。經(jīng)過系統(tǒng)梳理,目前中國各種乳品質(zhì)量安全相關(guān)的標(biāo)準(zhǔn)共160余項(xiàng)(含已發(fā)布和正在制訂過程中).通過分析標(biāo)準(zhǔn)存在的問題,開展與國際標(biāo)準(zhǔn)的對比研究,并結(jié)合中國生產(chǎn)和消費(fèi)的國情,提出了新的乳品質(zhì)量安全標(biāo)準(zhǔn)框架和目錄。清理后的標(biāo)準(zhǔn)共三大類75項(xiàng),分為產(chǎn)品標(biāo)準(zhǔn)17項(xiàng)、生產(chǎn)規(guī)范2項(xiàng)、檢驗(yàn)方法標(biāo)準(zhǔn)56項(xiàng)。
盡管新《乳標(biāo)》更科學(xué),但仍存在術(shù)語標(biāo)準(zhǔn)與國際通用標(biāo)準(zhǔn)不接軌的問題。正是這種結(jié)構(gòu)性缺陷,致使國家標(biāo)準(zhǔn)總是只能勉強(qiáng)應(yīng)對"發(fā)生一個(gè)問題補(bǔ)救一個(gè)問題",而缺少應(yīng)有的前瞻性和指導(dǎo)性,以至于喪失了食品安全控制的主動權(quán)。
對乳品標(biāo)準(zhǔn)體系頗有研究的顧佳升向CBN發(fā)表上述觀點(diǎn)。顧佳升舉例說,以"乳"為例,國際乳業(yè)聯(lián)合會(IDF)的定義是"不準(zhǔn)任何添加或提取,經(jīng)一次或多次擠自哺乳動物正常乳腺的分泌物".對比之下,我國定義缺少了"不準(zhǔn)任何添加或提取"的禁令性條款。之所以砍掉"不準(zhǔn)任何添加或提取",據(jù)稱是緣于無法"檢驗(yàn)".
"或許這也是我國前一時(shí)期大量出現(xiàn)違規(guī)違法'摻水摻假',甚至摻入'三聚氰胺'現(xiàn)象背后的深層原因之一。"顧佳升一針見血地指出。
國際通用標(biāo)準(zhǔn)中對上述基本術(shù)語的定義標(biāo)準(zhǔn)界定得相當(dāng)嚴(yán)格,各類"乳"不僅定義明確,而且各自的用途和適用的加工工藝也十分明晰,因而所得的終端成品不會在市場里發(fā)生混淆。
鑒于此,顧佳升建議,新《乳標(biāo)》正式出臺時(shí),應(yīng)在國家基礎(chǔ)標(biāo)準(zhǔn)層面上恢復(fù)砍掉的"禁令性條款","改變當(dāng)前社會單純依賴'檢驗(yàn)把關(guān)'監(jiān)管食品安全的思維定勢顯得迫在眉睫".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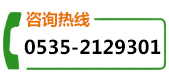


 掃描二維碼 分享好友和朋友圈
掃描二維碼 分享好友和朋友圈

 魯公網(wǎng)安備 37060202000128號
魯公網(wǎng)安備 37060202000128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