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標(biāo)準(zhǔn)出臺(tái)過程令人費(fèi)解,關(guān)鍵指標(biāo)的顯著降低讓人驚訝,而非止一處的標(biāo)準(zhǔn)模糊或硬傷,令人擔(dān)憂其是否堪當(dāng)整飭乳業(yè)的重任
6月11日,北京京西賓館。
來自商務(wù)部、衛(wèi)生部等中央部委的數(shù)十名官員共商食品安全議題。一名聽眾當(dāng)場(chǎng)質(zhì)問國(guó)家食品藥品監(jiān)管局食品安全監(jiān)管司司長(zhǎng)徐景和:“食品安全監(jiān)管到底誰(shuí)說了算?究竟能不能管好?管不好應(yīng)該如何問責(zé)?”徐景和一時(shí)語(yǔ)塞。
在食品安全成為重大公共話題之際,由衛(wèi)生部牽頭制定,今年4月下旬公布、6月陸續(xù)開始實(shí)施的《生乳》等66項(xiàng)新乳品安全國(guó)家標(biāo)準(zhǔn)(下稱“新國(guó)標(biāo)”),自公布之日起即引起行業(yè)震動(dòng),其中不乏亮點(diǎn),但同時(shí)飽受行業(yè)內(nèi)外爭(zhēng)議和責(zé)問。
“新國(guó)標(biāo)”取消了1986年“國(guó)標(biāo)”中生鮮乳收購(gòu)標(biāo)準(zhǔn)的四個(gè)等級(jí),只設(shè)最低限度。尤其是生乳收購(gòu)標(biāo)準(zhǔn)中的蛋白質(zhì)最低值及微生物限量這兩項(xiàng)核心指標(biāo),與1986年相比顯著降低。
1986年“國(guó)標(biāo)”中,就必須優(yōu)先遵照、因此最具可比性的生鮮乳第一等級(jí)而言,規(guī)定蛋白質(zhì)最低值為2.95%,而2010年“新國(guó)標(biāo)”設(shè)定蛋白質(zhì)最低值為2.8%。中國(guó)主要奶牛品種為荷斯坦奶牛,在國(guó)際奶牛養(yǎng)殖界,通常認(rèn)定這種奶牛的蛋白質(zhì)最低值為3.18%。
1986年“國(guó)標(biāo)”中,生鮮乳第一等級(jí)的微生物限量為每毫升50萬(wàn)個(gè);“新國(guó)標(biāo)”微生物限量為每毫升200萬(wàn)個(gè)。美國(guó)、歐盟生鮮乳微生物限量為每毫升小于10萬(wàn)個(gè),香港的限量為每毫升小于20萬(wàn)個(gè),丹麥一級(jí)奶的微生物限量為每毫升小于10萬(wàn)個(gè),優(yōu)級(jí)奶則為每毫升小于3萬(wàn)個(gè)。
1986年“國(guó)標(biāo)”與國(guó)際標(biāo)準(zhǔn)已有明顯差距,2010年標(biāo)準(zhǔn)在其基礎(chǔ)上又大幅降低。不少乳業(yè)界人士直斥“新國(guó)標(biāo)”是“歷史性倒退”。
中國(guó)奶業(yè)完了,新標(biāo)準(zhǔn)名義上照顧奶農(nóng)利益,實(shí)際上卻把牛奶搞得亂七八糟。”中國(guó)畜產(chǎn)品加工科技事業(yè)的開拓者和奠基人、國(guó)務(wù)院學(xué)位委員會(huì)學(xué)科組成員、享有中國(guó)“乳業(yè)泰斗”之譽(yù)的駱承庠對(duì)記者表示。
“全世界恐怕都沒有這樣低的指標(biāo)。”曾參與“新國(guó)標(biāo)”討論的上海奶業(yè)行業(yè)協(xié)會(huì)副秘書長(zhǎng)顧佳升認(rèn)為。
利拉伐(上海)乳業(yè)機(jī)械有限公司總經(jīng)理張家淇亦稱,新標(biāo)準(zhǔn)與科學(xué)化飼養(yǎng)奶牛、提高奶牛品質(zhì)單產(chǎn)的產(chǎn)業(yè)初衷相背離。“既然隨便飼養(yǎng)都能合格,農(nóng)民還有什么動(dòng)力改善質(zhì)量。”5月中旬,在綿陽(yáng)舉行的一次乳業(yè)發(fā)展論壇上,張家淇對(duì)記者表示,長(zhǎng)遠(yuǎn)來看,“新國(guó)標(biāo)”可能造成的遺患將難以消弭。
作為食品衛(wèi)生標(biāo)準(zhǔn)的一個(gè)試點(diǎn),乳業(yè)新標(biāo)準(zhǔn)的制定有望給整個(gè)食品安全新標(biāo)準(zhǔn)探路。而對(duì)于尚未完全從三聚氰胺事件沉重打擊中恢復(fù)過來的中國(guó)乳業(yè),“新國(guó)標(biāo)”無(wú)疑將影響其未來方向。
關(guān)鍵指標(biāo)的降低只是一個(gè)火藥引子,在專業(yè)人士眼里,“新國(guó)標(biāo)”中非止一處的模糊界定甚至明顯硬傷,令人擔(dān)憂其是否堪當(dāng)整飭乳業(yè)的重任。
經(jīng)過最近“黃金十年”的快速發(fā)展,雖有行業(yè)丑聞困擾,且受經(jīng)濟(jì)低迷打壓,中國(guó)乳業(yè)的發(fā)展速度仍然穩(wěn)健。
據(jù)中國(guó)乳制品工業(yè)協(xié)會(huì)今年4月公布的數(shù)字:2009年全國(guó)規(guī)模以上乳制品企業(yè)工業(yè)總產(chǎn)值累計(jì)1650.2億元,同比增長(zhǎng)12.38%,乳制品總產(chǎn)量1935.1萬(wàn)噸,同比增長(zhǎng)12.88%。如此涉及數(shù)億消費(fèi)者的千億元規(guī)模的行業(yè),國(guó)家標(biāo)準(zhǔn)的些微改動(dòng),均易牽涉各方力量與利益的復(fù)雜博弈。
火線任務(wù)
2007年年初,衛(wèi)生部即開始組織有關(guān)部門對(duì)中國(guó)現(xiàn)行乳與乳制品標(biāo)準(zhǔn)進(jìn)行清理與歸并,籌備制訂乳業(yè)“新國(guó)標(biāo)”,但進(jìn)展甚緩。
2008年9月,三鹿事件爆發(fā)。次月9日,國(guó)務(wù)院火速出臺(tái)《乳品質(zhì)量安全監(jiān)督管理?xiàng)l例》,其中規(guī)定:“縣級(jí)以上人民政府衛(wèi)生行政部門依照職權(quán)負(fù)責(zé)乳品質(zhì)量安全監(jiān)督管理的綜合協(xié)調(diào)、組織查處食品安全重大事故的職責(zé),并賦予衛(wèi)生部組織制定乳品質(zhì)量安全國(guó)家標(biāo)準(zhǔn)的責(zé)任。”
當(dāng)月,衛(wèi)生部就召集乳品企業(yè)加工代表及衛(wèi)生系統(tǒng)專家,參與制訂乳業(yè)新標(biāo)準(zhǔn)。知情者回憶,此次會(huì)議上,專家對(duì)于乳業(yè)標(biāo)準(zhǔn)制訂歸屬權(quán)爭(zhēng)論尤為激烈,反對(duì)者稱,標(biāo)準(zhǔn)制訂者應(yīng)為奶牛養(yǎng)殖歸口單位農(nóng)業(yè)部,而非對(duì)乳業(yè)并不熟悉的衛(wèi)生部。
11月,不甚明晰情況的衛(wèi)生部提出,生乳標(biāo)準(zhǔn)以農(nóng)業(yè)部意見為主,并希望農(nóng)業(yè)部每月單獨(dú)例會(huì)討論后反饋意見。
由于乳業(yè)涉及部門眾多,2008年12月開始,衛(wèi)生部會(huì)同農(nóng)業(yè)部、國(guó)家標(biāo)準(zhǔn)委、工業(yè)和信息化部、工商總局、質(zhì)檢總局、食品藥品監(jiān)管局、中國(guó)疾病預(yù)防控制中心、輕工業(yè)聯(lián)合會(huì)、中國(guó)乳制品工業(yè)協(xié)會(huì)、中國(guó)奶業(yè)協(xié)會(huì)等機(jī)構(gòu),成立了乳品安全標(biāo)準(zhǔn)工作協(xié)調(diào)小組和乳品安全標(biāo)準(zhǔn)工作專家組,正式開展標(biāo)準(zhǔn)制修訂工作。
衛(wèi)生部副部長(zhǎng)陳嘯宏擔(dān)任協(xié)調(diào)小組組長(zhǎng),農(nóng)業(yè)部副部長(zhǎng)陳曉華、國(guó)家標(biāo)準(zhǔn)委副主任孫曉康等擔(dān)任協(xié)調(diào)小組副組長(zhǎng)。專家組組長(zhǎng)由中國(guó)疾病預(yù)防控制中心營(yíng)養(yǎng)與食品安全所副所長(zhǎng)王竹天擔(dān)任。逾70名專家成員來自相關(guān)部委、大專院校及乳品企業(yè)。
記者獲悉,“新國(guó)標(biāo)”具體起草任務(wù)由衛(wèi)生部監(jiān)督局委托衛(wèi)生部疾病預(yù)防控制中心營(yíng)養(yǎng)與食品安全所承擔(dān),參與起草的人數(shù)超過70人,標(biāo)準(zhǔn)分設(shè)乳品產(chǎn)品、嬰幼兒配方食品、理化檢測(cè)方法、微生物檢測(cè)方法及乳品生產(chǎn)規(guī)范五個(gè)工作組,參與討論人數(shù)超過600人。
2008年12月29日,衛(wèi)生部聯(lián)合農(nóng)業(yè)部、國(guó)家標(biāo)準(zhǔn)委等部門在京召開乳品質(zhì)量安全標(biāo)準(zhǔn)工作第一次協(xié)調(diào)小組會(huì)議,會(huì)議決定,標(biāo)準(zhǔn)制訂工作分四個(gè)階段開展。
第一階段為準(zhǔn)備階段,時(shí)間為2008年12月末起到2009年2月,主要工作是調(diào)查和分析現(xiàn)行乳品標(biāo)準(zhǔn)存在的問題,參照國(guó)際標(biāo)準(zhǔn)的框架和原則,擬定乳品質(zhì)量安全標(biāo)準(zhǔn)框架和制修訂原則。第二階段為制修訂標(biāo)準(zhǔn)階段,時(shí)間為2009年2月-5月。第三階段為廣泛征求意見階段,時(shí)間為6月-7月,包括社會(huì)征求意見和世貿(mào)組織成員征求意見。第四階段為標(biāo)準(zhǔn)批準(zhǔn)程序,時(shí)間為2009年8月-9月。
但衛(wèi)生部整體協(xié)調(diào)工作費(fèi)時(shí)費(fèi)力,導(dǎo)致標(biāo)準(zhǔn)進(jìn)展一再拖延。
2009年6月1日起施行的《中華人民共和國(guó)食品安全法》再次認(rèn)定了衛(wèi)生部作為標(biāo)準(zhǔn)起草者的主體地位。
該法規(guī)定:“國(guó)務(wù)院設(shè)立食品安全委員會(huì),其工作職責(zé)由國(guó)務(wù)院規(guī)定。國(guó)務(wù)院衛(wèi)生行政部門承擔(dān)食品安全綜合協(xié)調(diào)職責(zé),負(fù)責(zé)食品安全風(fēng)險(xiǎn)評(píng)估、食品安全標(biāo)準(zhǔn)制定、食品安全信息公布、食品檢驗(yàn)機(jī)構(gòu)的資質(zhì)認(rèn)定條件和檢驗(yàn)規(guī)范的制定,組織查處食品安全重大事故。”
直至2009年底,標(biāo)準(zhǔn)起草實(shí)際工作方見起色。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,2009年12月,陜西金橋乳業(yè)、上海熊貓乳品有限公司再次爆出生產(chǎn)銷售三聚氰胺超標(biāo)產(chǎn)品丑聞,國(guó)務(wù)院責(zé)令乳業(yè)“新國(guó)標(biāo)”早日出臺(tái)。
至2010年2月6日,國(guó)務(wù)院又高調(diào)設(shè)立國(guó)務(wù)院食品安全委員會(huì)。作為國(guó)務(wù)院食品安全工作的高層次議事協(xié)調(diào)機(jī)構(gòu),共有15個(gè)部門參加,由國(guó)務(wù)院副總理李克強(qiáng)任主任,國(guó)務(wù)院副總理回良玉、王岐山任副主任。重壓之下,國(guó)務(wù)院食品安全委員會(huì)第一次全體會(huì)議召開。
在此形勢(shì)下,乳業(yè)安全新標(biāo)準(zhǔn),被當(dāng)做食品安全標(biāo)準(zhǔn)制定的試點(diǎn),出臺(tái)緊迫性日甚一日。
應(yīng)急而生
標(biāo)準(zhǔn)參與討論者上海奶業(yè)行業(yè)協(xié)會(huì)副秘書長(zhǎng)顧佳升稱,在眾多標(biāo)準(zhǔn)中,耗時(shí)最久的是《生乳》標(biāo)準(zhǔn),而熟悉情況的農(nóng)業(yè)部幾乎沒有參與。“衛(wèi)生部并不了解奶業(yè)的實(shí)際情況,導(dǎo)致會(huì)議多數(shù)時(shí)間浪費(fèi)在無(wú)意義的討論上,使得標(biāo)準(zhǔn)推出時(shí)間大大延期。”顧佳升告訴記者。
農(nóng)業(yè)部乳品質(zhì)量監(jiān)督檢驗(yàn)測(cè)試中心高工程師張宗城說,與會(huì)專家普遍對(duì)奶業(yè)狀況缺乏了解,迫于時(shí)間壓力,最終的工作只是對(duì)數(shù)千項(xiàng)指標(biāo)的整理合并。
在會(huì)議上,與會(huì)專家多是各省疾控中心的官員,主要討論的是如何合并的問題,而沒有借鑒提高。“很多都是原封不動(dòng)地合并,所以工作量并不大。”張宗城回憶道。
會(huì)議對(duì)既有的混亂體系做了歸納修訂,以黃青霉素為例,既有法規(guī)中,對(duì)指標(biāo)檢測(cè)的不同規(guī)定就達(dá)五種,對(duì)乳品脂肪含量的不同規(guī)定亦達(dá)三種。
在標(biāo)準(zhǔn)制訂過程中,一稿至三稿的評(píng)審均秘密進(jìn)行,并未廣泛征求意見,只在最后一稿進(jìn)行了公示。在整個(gè)過程中,衛(wèi)生部沒有主動(dòng)征求奶農(nóng)意見。
征求意見稿的統(tǒng)一過程耗時(shí)甚久,臨近截稿,各類反饋意見仍未能逐一采納,衛(wèi)生部不得已最終采用“一刀切”的辦法。
衛(wèi)生部最終在對(duì)160余項(xiàng)現(xiàn)行和正在制訂中的乳品相關(guān)標(biāo)準(zhǔn)進(jìn)行分析和討論的基礎(chǔ)上,形成了75項(xiàng)乳品安全國(guó)家標(biāo)準(zhǔn),包括產(chǎn)品標(biāo)準(zhǔn)、生產(chǎn)規(guī)范和檢測(cè)方法標(biāo)準(zhǔn)三大類,其中產(chǎn)品標(biāo)準(zhǔn)17項(xiàng),生產(chǎn)規(guī)范2項(xiàng),檢測(cè)方法56項(xiàng)。
其中66項(xiàng)通過食品安全國(guó)家標(biāo)準(zhǔn)審評(píng)委員會(huì)的審查,發(fā)布為國(guó)家安全標(biāo)準(zhǔn)。
和原來160余項(xiàng)數(shù)量繁多、相互打架的乳品“國(guó)標(biāo)”相比,現(xiàn)在頒布的66項(xiàng)標(biāo)準(zhǔn)大為精簡(jiǎn),其中值得稱道的是,吸納了原屬于“政府規(guī)章制度”的關(guān)于“液態(tài)乳標(biāo)鮮、標(biāo)純、標(biāo)復(fù)原”的“三標(biāo)”內(nèi)容,大大提升了這項(xiàng)規(guī)定的法律地位,這使得消費(fèi)者可通過各類標(biāo)識(shí)一目了然地區(qū)分市場(chǎng)上的各種液態(tài)奶。
前全國(guó)食品工業(yè)標(biāo)準(zhǔn)化技術(shù)委員會(huì)秘書長(zhǎng)郝煜稱,作為目前惟一強(qiáng)制執(zhí)行的標(biāo)準(zhǔn),“新國(guó)標(biāo)”最大遺憾是“守舊”。
專家組工作的原則只是“整合梳理”,因而缺乏應(yīng)有的“與時(shí)俱進(jìn)”動(dòng)力。
同時(shí),“新國(guó)標(biāo)”沒有注明起草單位、參與起草人及后續(xù)承擔(dān)宣傳解釋的對(duì)應(yīng)部門。“這種不符合立法規(guī)范的情況在乳業(yè)歷史上還是頭一回。”一名熟悉乳業(yè)相關(guān)法律法規(guī)起草規(guī)程的內(nèi)部人士稱。
記者多次向衛(wèi)生部提出采訪要求,但截至發(fā)稿,亦未獲安排。一位衛(wèi)生部官員告訴記者,鑒于乳業(yè)標(biāo)準(zhǔn)已引起行業(yè)內(nèi)外巨大爭(zhēng)議,衛(wèi)生部將于近期組織一次媒體交流會(huì),就相關(guān)問題進(jìn)行說明。
受質(zhì)疑的專業(yè)性
長(zhǎng)久以來,奶業(yè)管理沿襲前蘇聯(lián)模式,行政權(quán)力條狀分割非常明顯,涉及部門多達(dá)15個(gè),質(zhì)檢總局負(fù)責(zé)制定產(chǎn)品標(biāo)準(zhǔn),衛(wèi)生部門制定衛(wèi)生標(biāo)準(zhǔn),農(nóng)業(yè)部門制定農(nóng)業(yè)標(biāo)準(zhǔn),商務(wù)部門制定商業(yè)標(biāo)準(zhǔn),工信部制定加工標(biāo)準(zhǔn),這些標(biāo)準(zhǔn)常有相互抵觸之處。生乳標(biāo)準(zhǔn)的話語(yǔ)權(quán)歷來不在最為熟悉情況的農(nóng)業(yè)部,而在其他各類主管部門。
“這導(dǎo)致眾多政策推行不力,問責(zé)不清。”中國(guó)奶業(yè)協(xié)會(huì)副理事長(zhǎng)王懷寶稱,以學(xué)生奶為例,推行十年普及率至今不足2%。
政出多門導(dǎo)致各主管部門的專業(yè)能力缺乏。“衛(wèi)生部專家知識(shí)背景多是公共衛(wèi)生和分析檢驗(yàn),但缺乏乳品行業(yè)背景尤其是乳品工藝,因而導(dǎo)致很多標(biāo)準(zhǔn)避重就輕。”顧佳升稱。
專業(yè)性不足導(dǎo)致乳業(yè)“新國(guó)標(biāo)”體系結(jié)構(gòu)與國(guó)際標(biāo)準(zhǔn)存在很大不同,國(guó)內(nèi)以最終的產(chǎn)品標(biāo)準(zhǔn)為主,檢驗(yàn)方法也是為終端成品“把關(guān)”需要而配置的。術(shù)語(yǔ)標(biāo)準(zhǔn)和工藝標(biāo)準(zhǔn)則幾乎是空白。而國(guó)際標(biāo)準(zhǔn)體系的結(jié)構(gòu)則主要由三個(gè)部分組成:專業(yè)術(shù)語(yǔ)定義、生產(chǎn)和加工過程工藝、檢驗(yàn)方法,產(chǎn)品成品標(biāo)準(zhǔn)退居其次。
一名三元乳業(yè)的高管表示,“新國(guó)標(biāo)”規(guī)定生乳是“健康奶畜所產(chǎn)”,但究竟什么是“健康奶畜”卻缺乏明確規(guī)定,在檢測(cè)指標(biāo)里,也未對(duì)用于判定是否健康奶畜的體細(xì)胞檢測(cè)作出規(guī)定。
另外對(duì)于一些重要參數(shù)缺乏基礎(chǔ)研究依據(jù),例如“200萬(wàn)微生物含量”依據(jù)何來。“很多東西看起來是拍腦袋決定的。這就不是一個(gè)很完善的標(biāo)準(zhǔn),合理性大打折扣。”上述三元高管表示。
“新國(guó)標(biāo)”中關(guān)于生產(chǎn)工藝的規(guī)范只有寥寥兩項(xiàng),且含混不清。例如《殺菌乳安全標(biāo)準(zhǔn)》,對(duì)究竟采用何種加工工藝、加熱溫度與受熱時(shí)間等關(guān)鍵元素指標(biāo)只字未提。“現(xiàn)在的標(biāo)準(zhǔn)是重檢測(cè)輕過程控制,本末倒置。”中國(guó)奶業(yè)協(xié)會(huì)原常務(wù)理事王丁棉稱。
乳品加工的基本原則是盡可能減少加工過程營(yíng)養(yǎng)的損失和有毒有害物質(zhì)的生成。在國(guó)際上,各國(guó)政府都對(duì)殺菌工藝過程進(jìn)行參數(shù)限定,并列入現(xiàn)場(chǎng)監(jiān)管范疇。
“新國(guó)標(biāo)”這種輕工藝過程的做法存在巨大安全隱患,例如超高溫瞬間滅菌技術(shù)(UHT)在加工過程中使用超高溫和長(zhǎng)時(shí)間存放會(huì)導(dǎo)致褐變,產(chǎn)生的有毒元素達(dá)到一定量可致癌。
王丁棉認(rèn)為,“新國(guó)標(biāo)”對(duì)乳品行業(yè)的核心加工要素——熱處理方法、強(qiáng)度不作具體規(guī)定,會(huì)導(dǎo)致企業(yè)濫用這一技術(shù)。過度熱處理不但使?fàn)I養(yǎng)損失,有害物質(zhì)大大增加,而且改變了乳的質(zhì)地與風(fēng)味,反過來促使企業(yè)使用穩(wěn)定劑和香料等食品添加劑,從而增加了乳品的不安全性。
但是這些建議均未得到采納。
據(jù)顧佳升統(tǒng)計(jì),世界上“乳與乳制品”不安全事件80%以上集中在“食品的物理、生物和化學(xué)三大危害”之一的“生物危害”上,而中國(guó)則幾乎集中在“化學(xué)危害”。他認(rèn)為這與乳企特別偏愛通過“過度熱處理”殺滅乳品細(xì)菌,進(jìn)而在過程中添加香料改進(jìn)口感息息相關(guān)。
誰(shuí)在推動(dòng)標(biāo)準(zhǔn)降低
生乳“新國(guó)標(biāo)”關(guān)于蛋白質(zhì)及微生物含量?jī)身?xiàng)核心指標(biāo)趨低,引起業(yè)內(nèi)激烈反彈。
中國(guó)奶業(yè)協(xié)會(huì)乳品工業(yè)委員會(huì)副主任、中國(guó)畜產(chǎn)品加工研究會(huì)乳品加工委員會(huì)副主任、原“衛(wèi)生部全國(guó)乳與乳制品定標(biāo)組”副組長(zhǎng)曾壽瀛對(duì)《財(cái)經(jīng)》記者表示,“沒有好面蒸不出好饅頭。原料奶蛋白質(zhì)含量降低帶來的不是一般的問題,會(huì)帶來乳品加工行業(yè)一系列的深層次問題。”
曾壽瀛回憶,早在2009年6月19日召開的全國(guó)乳品安全委員會(huì)工作會(huì)議前,關(guān)于蛋白質(zhì)含量標(biāo)準(zhǔn)的討論已有十余次,絕大多數(shù)與會(huì)者支持沿用原來的2.95%標(biāo)準(zhǔn)。兩大乳業(yè)巨頭蒙牛和伊利則屬于“降低派”。會(huì)議主持人動(dòng)員曾壽瀛宣講維持2.95%的必要性。
“一直到8月底,所有專家委員會(huì)成員都再也沒有對(duì)蛋白質(zhì)的標(biāo)準(zhǔn)提出異議。”曾壽瀛說。
但其后進(jìn)展卻頗多變數(shù)。作為生乳“新國(guó)標(biāo)”后期的參與審稿者,曾壽瀛回憶,直至2009年8月底,在送交農(nóng)業(yè)部與衛(wèi)生部的審稿中,蛋白質(zhì)含量都是2.95%。10月20日,衛(wèi)生部網(wǎng)站上公布的征求意見稿的標(biāo)準(zhǔn)已經(jīng)修改為:每年5月至9月標(biāo)準(zhǔn)為2.8%,其余時(shí)間為2.95%。
到2010年4月22日“新國(guó)標(biāo)”正式網(wǎng)上公布時(shí),標(biāo)準(zhǔn)已悄然變?yōu)?.8%。
“短短幾個(gè)月為什么會(huì)發(fā)生如此大的變化,我問了其他參與審稿的人,沒有一個(gè)人能說得清楚。作為制訂參與者,我們沒有裁決權(quán),甚至連一點(diǎn)知情權(quán)都沒有。”曾壽瀛說。
這一重大更改事前沒有通知,事后也沒有任何解釋,變更原因至今未明。
就生乳標(biāo)準(zhǔn)與衛(wèi)生部有過密切配合的一位農(nóng)業(yè)部官員表示,衛(wèi)生部將2.8%確定為“新國(guó)標(biāo)”這一決策的不透明性,他也不理解。
記者獲悉,將蛋白質(zhì)最低值標(biāo)準(zhǔn)降至2.8%的最大推動(dòng)力,來自農(nóng)業(yè)部。
農(nóng)業(yè)部畜牧業(yè)司副巡視員、奶業(yè)管理辦公室主任王俊勛接受記者采訪時(shí)表示,“拋開現(xiàn)在的論爭(zhēng),“新國(guó)標(biāo)”會(huì)在今后的實(shí)踐中得到檢驗(yàn)。”他認(rèn)為,標(biāo)準(zhǔn)的高和低只是看法問題,標(biāo)準(zhǔn)低并不代表不正視問題。
王俊勛透露,2008年10月,衛(wèi)生部首次與農(nóng)業(yè)部討論的就是原奶收購(gòu)標(biāo)準(zhǔn)。在標(biāo)準(zhǔn)起草之初,衛(wèi)生部曾希望提高原奶收購(gòu)標(biāo)準(zhǔn),但農(nóng)業(yè)部認(rèn)為在現(xiàn)有時(shí)機(jī)提高原奶收購(gòu)標(biāo)準(zhǔn)并不合適。
農(nóng)業(yè)部奶業(yè)管理辦公室成立于2008年10月24日。此前農(nóng)業(yè)部對(duì)全國(guó)原奶整體指標(biāo)也缺乏了解。為了配合完成生乳標(biāo)準(zhǔn)制訂,王俊勛迫在眉睫的工作就是收集原奶收購(gòu)方的各類數(shù)據(jù)。
在其努力下,農(nóng)業(yè)部一年之內(nèi)收集到十余萬(wàn)個(gè)原奶收購(gòu)數(shù)據(jù),這些來自國(guó)內(nèi)規(guī)模較大的乳品企業(yè)、第三方渠道以及奶站的基礎(chǔ)數(shù)據(jù),對(duì)于標(biāo)準(zhǔn)最終確定發(fā)揮了重要作用。
農(nóng)業(yè)部調(diào)查數(shù)據(jù)顯示,國(guó)內(nèi)最大的一些乳品加工企業(yè),夏天時(shí)蛋白質(zhì)含量基本都達(dá)不到2.95%,個(gè)別情況下甚至低至2.26%,達(dá)標(biāo)的企業(yè)寥寥無(wú)幾。“沒有哪個(gè)企業(yè)敢說它沒有收過2.95%以下的牛奶,與其桌面下偷偷摸摸做,不如把事情拿到桌面上解決。2.8%就是立足國(guó)情實(shí)事求是。”王俊勛稱。
中國(guó)奶協(xié)數(shù)據(jù)顯示,國(guó)內(nèi)奶牛養(yǎng)殖仍以小規(guī)模散養(yǎng)為主,1頭-5頭奶牛農(nóng)戶比例達(dá)78%,6頭-20頭所占比例約13%,其散養(yǎng)規(guī)模占全國(guó)奶牛總存欄量的80%-90%,王俊勛稱,“短時(shí)間內(nèi)扭轉(zhuǎn)這種局面是不切合實(shí)際的。”
另一項(xiàng)中國(guó)奶協(xié)調(diào)研數(shù)據(jù)顯示,2009年3月,全國(guó)奶牛養(yǎng)殖戶虧損面超過50%,黑龍江省一度達(dá)到75%,時(shí)至今日,虧損面尚有35%。“奶業(yè)需要的是休養(yǎng)生息,長(zhǎng)此下去整個(gè)產(chǎn)業(yè)基礎(chǔ)就全沒了。”王俊勛表示。
他認(rèn)為,蛋白質(zhì)含量標(biāo)準(zhǔn)設(shè)置太高會(huì)危及奶農(nóng)生存。在既有利益分配格局中,對(duì)奶農(nóng)而言,尚無(wú)一個(gè)合理退出機(jī)制,不甘被動(dòng)退出的人會(huì)以造假形式蒙混過關(guān),從而引發(fā)質(zhì)量隱患。
達(dá)能營(yíng)養(yǎng)中心(中國(guó))總代表張國(guó)雄也主張,相對(duì)寬松的標(biāo)準(zhǔn),可以避免奶農(nóng)作假。以微生物含量為例,他認(rèn)為,在既有飼養(yǎng)水平?jīng)]有改善的情況下,過高的標(biāo)準(zhǔn)會(huì)刺激更多危險(xiǎn)行為,一些奶牛飼養(yǎng)者可能會(huì)采用臭氧消毒滅菌的辦法,在此過程中會(huì)產(chǎn)生致癌溴化物。
王俊勛甚至認(rèn)為,2.8%的標(biāo)準(zhǔn)其實(shí)亦顯多余。之所以還要規(guī)定蛋白質(zhì)最低值,是由于《乳品質(zhì)量安全管理?xiàng)l例》中明確規(guī)定要制定乳品的“質(zhì)量安全標(biāo)準(zhǔn)”。“不僅是安全標(biāo)準(zhǔn),也有質(zhì)量標(biāo)準(zhǔn)。”
“不管蛋白質(zhì)高低,牛奶都是可以飲用的。不同的原奶可以生產(chǎn)不同的產(chǎn)品。不應(yīng)該將一部分奶農(nóng)排除在市場(chǎng)以外。這里面也有維穩(wěn)的因素。”王俊勛表示。
對(duì)于農(nóng)業(yè)部降低標(biāo)準(zhǔn)的主張,全球最大乳制品包裝企業(yè)利樂公司中國(guó)副總裁楊斌認(rèn)為,監(jiān)管部門把民生問題與產(chǎn)業(yè)發(fā)展問題相混淆了。“保護(hù)弱勢(shì)群體是否必須以犧牲整個(gè)產(chǎn)業(yè)安全和消費(fèi)者利益為代價(jià),這種做法值得商榷。”
內(nèi)蒙古奶聯(lián)科技有限公司董事、副總經(jīng)理李兆林認(rèn)為,標(biāo)準(zhǔn)的降低使收奶范圍放寬,變相地為養(yǎng)殖水平低的農(nóng)民散戶養(yǎng)牛開綠燈,短期內(nèi)有利于農(nóng)民增收,長(zhǎng)遠(yuǎn)來看與國(guó)家推行規(guī)模化飼養(yǎng)并不匹配。
隱現(xiàn)利益博弈
在標(biāo)準(zhǔn)降低的背后,一些業(yè)內(nèi)人士多次提及蒙牛、伊利兩大乳業(yè)巨頭的表現(xiàn)。
一位知情者透露,在標(biāo)準(zhǔn)討論過程中,伊利負(fù)責(zé)奶源的會(huì)議代表曾表示,按照現(xiàn)行2.95%標(biāo)準(zhǔn),內(nèi)蒙古、黑龍江分別有10%、6%原奶無(wú)法達(dá)標(biāo),河北亦有相當(dāng)比例原奶無(wú)法合格,全國(guó)數(shù)量更為驚人,以此希望降低標(biāo)準(zhǔn)。
蒙牛、伊利兩者共占據(jù)中國(guó)乳業(yè)市場(chǎng)31%份額,且增勢(shì)兇猛。
“如果蒙牛、伊利的牛奶都不合格,監(jiān)管部門會(huì)懷疑標(biāo)準(zhǔn)制定的普遍適用性,如此大的體量使得監(jiān)管部門不得不參考其意見。”一名知情者稱。
據(jù)稱蒙牛也希望“國(guó)標(biāo)”放寬口子。針對(duì)衛(wèi)生部網(wǎng)上公布的乳業(yè)標(biāo)準(zhǔn)公開征求意見稿,有消息稱蒙牛曾提供反饋意見,希望將細(xì)菌含量放寬至每毫升1000萬(wàn)個(gè)。這幾乎是歐盟標(biāo)準(zhǔn)的100倍。
但蒙牛方面對(duì)記者堅(jiān)決否認(rèn)有過上述主張,相關(guān)人士解釋道,蒙牛目前可控奶源占其全部奶源的70%以上,并要以更高品質(zhì)標(biāo)準(zhǔn)來贏得市場(chǎng),無(wú)須主張降低標(biāo)準(zhǔn)。
全國(guó)乳業(yè)目前50%以上均是手工擠奶,剛擠下的原奶中微生物含量一般每亳升不超過30萬(wàn)個(gè),微生物超標(biāo)的原因主要是二次污染及疾病。一旦當(dāng)?shù)厥召?gòu)半徑過大難以及時(shí)輻射,這些牛奶通常會(huì)存放在奶罐中一到兩天甚至更久。
與蒙牛方面提供的數(shù)據(jù)相反,業(yè)內(nèi)人士認(rèn)為蒙牛對(duì)散戶奶源的依賴性極強(qiáng)。降低細(xì)菌標(biāo)準(zhǔn),客觀上它是受益的,可以借此擴(kuò)大收購(gòu)半徑,緩解原料匱乏壓力,并降低原奶收購(gòu)成本。
即使是一些看起來有進(jìn)步意義的標(biāo)準(zhǔn),在實(shí)際制訂過程中,也不得不達(dá)成某種妥協(xié)。
在2009年8月5日和8月19日的專家組會(huì)議上,衛(wèi)生部決定引入原農(nóng)業(yè)部和質(zhì)檢總局關(guān)于“三標(biāo)”的規(guī)定內(nèi)容,將其提升至法律地位;同時(shí)在相應(yīng)乳品標(biāo)準(zhǔn)里,增加各種液態(tài)乳的基本特性描述和主要技術(shù)指標(biāo)等內(nèi)容,并配套設(shè)立相應(yīng)的檢驗(yàn)方法標(biāo)準(zhǔn),為具體落實(shí)“三標(biāo)”規(guī)定提供判別技術(shù)支撐。
但是,到了10月20日,在衛(wèi)生部網(wǎng)站公示的“乳品安全標(biāo)準(zhǔn)征求意見稿”里,各種液態(tài)乳基本特性描述和主要技術(shù)指標(biāo)內(nèi)容及相應(yīng)檢驗(yàn)方法標(biāo)準(zhǔn)均被刪除,僅保留了“三標(biāo)”內(nèi)容。
這一結(jié)果被業(yè)內(nèi)專家認(rèn)為有利于常溫奶的壯大。常溫奶占據(jù)著中國(guó)的90%乳品市場(chǎng)。而市場(chǎng)上的常溫奶40%-50%是用復(fù)原乳制成,并且只有極少數(shù)產(chǎn)品在包裝上標(biāo)明“復(fù)原”字樣。“消費(fèi)者從口感上很難知道這一點(diǎn)。如果知道了,很多人可能就會(huì)選擇不喝。”一位業(yè)內(nèi)知情者說。
蒙牛、伊利都是以常溫奶為主,主要生產(chǎn)“利樂包/枕”包裝、保質(zhì)時(shí)間長(zhǎng)的超高溫滅菌奶,借助強(qiáng)大營(yíng)銷攻勢(shì)占領(lǐng)市場(chǎng)。但其全國(guó)性銷售網(wǎng)絡(luò)及超長(zhǎng)供應(yīng)鏈?zhǔn)蛊淠軌蜻_(dá)到“標(biāo)鮮”標(biāo)準(zhǔn)的產(chǎn)品極少。“‘三標(biāo)’規(guī)范越詳細(xì),無(wú)疑越不利于它們的發(fā)展。”一位行業(yè)知情者說。
衛(wèi)生部食品安全綜合協(xié)調(diào)與衛(wèi)生監(jiān)督局一名官員曾對(duì)起草專家說:“標(biāo)準(zhǔn)是各方利益協(xié)調(diào)的產(chǎn)物,很遺憾有關(guān)工藝規(guī)范的內(nèi)容沒能保住,希望你們能夠理解。”
在標(biāo)準(zhǔn)起草的前期,蒙牛、伊利還負(fù)責(zé)起草了與乳品生產(chǎn)企業(yè)最為密切的三大產(chǎn)品標(biāo)準(zhǔn):《巴氏殺菌乳安全標(biāo)準(zhǔn)》和《滅菌乳安全標(biāo)準(zhǔn)》由蒙牛起草,《生鮮乳安全標(biāo)準(zhǔn)》由伊利起草。
盡管政府機(jī)構(gòu)邀請(qǐng)大型企業(yè)參與標(biāo)準(zhǔn)起草,不乏國(guó)際慣例,但蒙牛和伊利作為標(biāo)準(zhǔn)起草者的資格仍遭受質(zhì)疑。有人認(rèn)為與其發(fā)展規(guī)模相比,蒙牛這種奶業(yè)巨頭并未承擔(dān)應(yīng)有的社會(huì)責(zé)任,在三聚氰胺事件中也存在重大污點(diǎn)。
在由王丁棉組織的2009年7月17日中國(guó)(重慶)奶業(yè)高峰論壇上,來自全國(guó)20多個(gè)城市奶協(xié)、20多家乳品企業(yè)和數(shù)家大中院校的代表,在會(huì)上紛紛公開指責(zé)蒙牛、伊利在標(biāo)準(zhǔn)修訂過程中于己牟利。
“由常溫奶企業(yè)起草巴氏殺菌乳標(biāo)準(zhǔn),背后是利益集團(tuán)的影子。參與標(biāo)準(zhǔn)修訂的乳企顯然不愿意自我束縛手腳。”王丁棉稱,這導(dǎo)致在標(biāo)準(zhǔn)制訂過程中缺乏透明度,很多時(shí)候只是走程序。
國(guó)家科技進(jìn)步一等獎(jiǎng)獲得者、中國(guó)畜產(chǎn)品加工研究會(huì)名譽(yù)副會(huì)長(zhǎng)魏榮祿透露,蒙牛在起草之初即希望將“復(fù)原乳”一詞寫進(jìn)《巴氏殺菌乳安全標(biāo)準(zhǔn)》和《滅菌乳安全標(biāo)準(zhǔn)》中,以求將其法律化。而在定稿《滅菌乳安全標(biāo)準(zhǔn)》中,蒙牛成功使得“復(fù)原乳”成為“滅菌乳”定義的一部分。在該標(biāo)準(zhǔn)中,“超高溫滅菌乳”和“保持式滅菌乳”的定義都含有以下文字:“以生牛羊乳為原料,添加或不添加復(fù)原乳……”
“復(fù)原乳”一詞最終沒被寫進(jìn)《巴氏殺菌乳安全標(biāo)準(zhǔn)》中。但魏榮祿等業(yè)內(nèi)人士認(rèn)為,《巴氏殺菌乳安全標(biāo)準(zhǔn)》中,“巴氏奶”的定義——“僅以生牛羊乳為原料,經(jīng)巴氏殺菌等工序制得的液體產(chǎn)品”,由于定義模糊,最終可能為用復(fù)原乳制作巴氏奶提供了縫隙。
魏榮祿稱,“這個(gè)標(biāo)準(zhǔn)使蒙牛等大量用復(fù)原乳生產(chǎn)純牛奶的企業(yè),有可能撇開之前‘24號(hào)文’(2005年國(guó)務(wù)院出臺(tái)的《關(guān)于加強(qiáng)液態(tài)奶生產(chǎn)經(jīng)營(yíng)管理的通知》)關(guān)于必須標(biāo)注‘復(fù)原乳’名稱的規(guī)定;其次,用法律文件的形式,間接明確了巴氏奶陣營(yíng)可以使用復(fù)原乳生產(chǎn)巴氏奶,瓦解傳統(tǒng)巴氏奶廠家‘鮮’的核心賣點(diǎn)。”
2005年的“24號(hào)文”出臺(tái)之際,蒙牛和伊利就曾極力反對(duì)標(biāo)注“復(fù)原乳”。
作為復(fù)原乳的反對(duì)者,魏榮祿和顧佳升均沒被邀請(qǐng)參加該標(biāo)準(zhǔn)最終討論。2009年中在北京香山飯店舉行的閉門研討會(huì)上,魏“不請(qǐng)自來”到會(huì)場(chǎng)旁聽,在會(huì)上他提出標(biāo)準(zhǔn)要營(yíng)養(yǎng)和安全并重,大力倡導(dǎo)發(fā)展巴氏奶,遏制復(fù)原乳的畸形發(fā)展,但很快遭到各方駁斥——“一些人以會(huì)議討論的是安全問題、與營(yíng)養(yǎng)無(wú)關(guān)為由,根本不讓我發(fā)言。”
在2009年5月研討會(huì)議上,光明乳業(yè)牽頭制定的《酸奶安全標(biāo)準(zhǔn)》,曾遭到蒙牛、伊利炮轟。光明試圖將自己獨(dú)自掌握的一種無(wú)菌酸奶工藝寫進(jìn)標(biāo)準(zhǔn)之中,但蒙牛、伊利激烈反對(duì)在新標(biāo)準(zhǔn)中寫入這一新工藝。
在乳業(yè)標(biāo)準(zhǔn)的意見稿中,農(nóng)業(yè)部曾希望刪除鮮奶收購(gòu)中的“感官指標(biāo)”標(biāo)準(zhǔn),“它主觀性太強(qiáng),在操作中不可能有標(biāo)準(zhǔn)的眼睛和鼻子去看去聞,因此經(jīng)常被奶企用于原奶收購(gòu)時(shí)克扣奶農(nóng)。”但這一建議遭到蒙牛反對(duì),最終流產(chǎn)。
但對(duì)于上述情況,蒙牛、伊利最終均謝絕接受記者正式采訪,不愿進(jìn)行公開的回應(yīng)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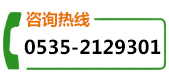


 掃描二維碼 分享好友和朋友圈
掃描二維碼 分享好友和朋友圈

 魯公網(wǎng)安備 37060202000128號(hào)
魯公網(wǎng)安備 37060202000128號(hào)